


对于“格子间动物”来说,砸烂办公室的情景已经在脑内发生n次。(图/《砸烂办公室》游戏截图)
作者 | 理查德·桑内特
编辑 | 谭山山
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的《没有面目的人》虽然出版于25年前,但书中所谈论的关于打工人的困境——在面对迅速被淘汰、被取代的可能性时,人们该如何进行自我定位,让今天的读者感同身受。
桑内特指出,在所谓“弹性资本主义”(flexible capitalism)制度下,工人必须灵活行事,对随时出现的变化持开放态度,不断承担风险,变得不再依赖规定和正式程序。随着这种对弹性的强调,工作(work)本身的意义以及我们用来形容的词汇也随之改变。
比如,在14世纪,“职务”(job)这个英文词指的是可以四处运送的一块或一片物品。如今的弹性制度,让“职务”这种晦涩难懂的意义重回视野,因为人们都在以片段的形式进行工作和劳动,终其一生都是如此。
“在一个心浮气躁、只看眼前的社会中,我们如何判断哪些是自我内在的持续价值?在一个专注实现短期目标的经济体系中,该如何去追求长期目标?在不断分裂又不断重组的机构组织中,该如何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忠诚与承诺?”桑内特如此发问。
本文摘选自《没有面目的人》,小标题为编选者所加。

《没有面目的人》
[美]理查德·桑内特 著 周悟拿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3-10
前不久,我在机场偶遇一位朋友。我称他为“瑞科”,我们已经15年未曾谋面。
我曾在25年前采访过他的父亲,当时我正在写一本关于美国蓝领工人的书《阶级中隐藏的伤害》。那时他的父亲恩里克做着一份清洁工的工作,对这个儿子寄予厚望。瑞科那时刚进入青春期,天资聪颖,而且是名运动健将。我和恩里克失去联络是在10年之后,那时瑞科刚在大学完成学业。
而在机场旅客休息室里出现的瑞科,手提时尚的皮制电脑包,炫耀着一枚顶部刻有图章的戒指。他穿的那件西装已经超过了我的购买力。看起来,他已经实现了父亲的梦想。
瑞科蔑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人,也看不起被官僚主义盔甲保护得严严实实的人;相反,他认为要乐于迎接变化,勇于承担风险。他也获得了成功;恩里克的收入位于薪资等级结构的底层,只超过全社会四分之一的人,而瑞科则已经攀升到了前5%的位置。但瑞科认为,他的故事也并没有那么幸福圆满。

乔治·克鲁尼在《在云端》中扮演一名几乎以机场为家的精英人士。(图/《在云端》剧照)
漂移
瑞科首先在当地一所大学的电子工程专业就读,毕业后去纽约的一所商学院继续深造,在那里遇见了未来的妻子。她和瑞科是同学,是一位家境较好的年轻新教徒。这对年轻夫妇的教育背景让他们做好了心理准备,以后也许会频繁地搬家换工作,后来事实也的确如此。在瑞科毕业后的14年职业生涯中,他已经搬了四次家。
硅谷计算机行业发展之初是一段振奋人心的时期,那时瑞科开始在西海岸的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担任技术顾问;然后他搬到了芝加哥,在那里也有不俗的工作表现。不过,他下一次搬家则是为了妻子的事业发展。如果瑞科是巴尔扎克笔下那种野心勃勃的人物,他绝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不但没有获得加薪,而且还离开了高科技活动的温床。
他转去了密苏里州的一处办公园区,那里虽然绿树成荫,但位置更加偏远。弗拉维亚离家工作时,恩里克多少感觉面上无光;瑞科则把妻子珍妮特视为平等的工作伙伴,并且已经适应她的节奏。就在珍妮特事业开始起飞的关头,他们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出生了。
在密苏里州的办公区,这个年轻人碰上了不确定的新经济形势,陷入困境。就在珍妮特得到晋升的时候,瑞科却被裁员了。他的公司被另一家更大的公司并购,而那家公司原来就有自己的分析员。因此,这对夫妇又搬了第四次家,回到东海岸的纽约郊区。珍妮特现在管理着一个会计师大团队,瑞科则创办了一家小型咨询公司。

《硅谷》讲述的是程序员的故事。(图/《硅谷》第六季剧照)
他们的发展势头都很不错,而且有很强的适应能力,能够互相支持,堪称是对模范夫妻。但是,夫妻双方都经常担心自己会轻易失去对生活的掌控能力,这种恐惧已经深深根植于他们的既往工作历程中。
就瑞科的情况而言,他对于失去掌控力的恐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涉及到时间管理。当瑞科告诉同辈伙伴他要创办自己的咨询公司时,大多数人都表示赞成;咨询公司似乎是一条迈向独立的路径。但在创业之初,他发现自己被一大堆琐碎任务吞没。
比如,他需要自己去复印,在此之前他只需要理所当然地拿到复印文件。他发现自己还陷入了无休无止的人际联络工作;每个电话都必须接听,每个泛泛之交都必须保持联系。为了拓展业务,他不得不跟随别人的时间表来行动,而那些人并没有义务搭理他。
正如我所说,我原本并不认为这对美国梦夫妇会让我感动到热泪盈眶。然而,当我和瑞科在飞机上共进晚餐,他开始更多地谈论个人生活,我也逐渐更多地共情起来。他对失去掌控的恐惧一步步发酵,比工作中失去权力的恐惧还要更深。他担心的是,为了在现代经济环境中生存,他需要采取的行动和遵循的生活方式已经使他的内在情感生活发生漂移。

《上班一条虫》里的办公室场景。(图/《上班一条虫》剧照)
偏见
现在的企业生存环境对中年充满了偏见,倾向于否认一个人过往经验的价值。企业文化会用赌场上的观念来看待中年人,认为他们只会规避风险。但我们很难反驳这种偏见,现代企业的世界总是压力爆表又动荡多变,中年人很可能会担心自己的内在价值被削弱了。
现代工作场所对年龄的态度有这样一个数据基础,即人们工作年限普遍缩短。美国55岁至64岁的男性中,1970 年的在职人数接近80%,1990 年已下降到65%。英国的数据和美国基本一致。在法国,中老年工作男性人数比例从约75%下降到接近40%,在德国则是从80%下降到接近50%。
早期进入职场的人数略有减少,因为年轻人日益重视教育,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晚了几年。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因此预测,在美国和西欧,“人们实际寿命约为75年至80年,而实际工作时间可能会变成24岁到54岁,即缩短为30年左右。”也就是说,工作寿命被缩短到不及生理寿命的一半,年长的员工在身体或精神出现不适之前,就已早早退出职场。

罗伯特·德尼罗在《实习生》中扮演高龄“实习生”。(图/《实习生》剧照)
强调年轻是工作寿命被压缩的结果之一。19 世纪的公司偏好雇用年轻人,因为他们是廉价劳动力。试想马萨诸塞州洛厄尔镇的“磨坊女孩”和英格兰北部的“矿坑男孩”,他们的工资远低于成人。在如今的资本主义中,雇主仍会出于低工资而偏好年轻人,世界欠发达地区的制造工厂和血汗工厂尤其如此。但现在更高层次的劳动力市场中,年轻人的其他特质似乎也让他们更具吸引力,而这更多是出于社会偏见。
例如,最近一期《加州管理评论》试图阐述弹性组织中年轻的好处和年老的坏处。文章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老员工心态僵化,规避风险,而且物理上也缺乏体力来应付弹性工作生活的各类要求。组织中的“朽木”形象也表达了这些根深蒂固的看法。
一位广告业的高管告诉社会学家凯瑟琳·纽曼:“在广告业,如果你已经年过三十,你就是死人一个。年龄是个杀手。”一位华尔街高管告诉她:“雇主们认为,如果你年过四十,你就已经丧失了思考能力。如果年过五十,他们会认为你已经精疲力尽。”弹性是“年轻”的同义词,而僵化则等同于“老去”。

有些行业如广告业,偏好采用年轻人。(图/《广告狂人》第一季剧照)
这些偏见会达到这样几个目的。例如,在公司重组过程中,雇主会把大龄员工归为随时可以遣散的人选。在过去的20年里,英美模式中40岁出头的男性员工被强制解雇的比例翻了一番。也正是因为企业会把年龄和僵化画等号,今天高管在50岁左右都面临要退休的压力,尽管他们的精神状态可能正处于巅峰。
比起刚步入职场的员工,年长又经验丰富的员工更容易对上司发表点评。因为他们积累了经验,这让他们具有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n)所说的“话语权”。这意味着,老员工对于他们眼中不够明智的决策,会更倾向于直言不满。他们这样做往往是出于对组织的忠诚,而不是对具体某位上司的忠诚。许多年轻员工接受到错误指令时,会表现得更加宽容。如果他们心有不忿,则更可能选择辞职,而不是留在公司内部进行抗争。就如赫希曼所言,他们更容易“离场”。
对于老员工来说,对年龄的偏见传达出一条强有力的信息:一个人的经验逐步积累,却会失去价值。当上级要求做出改革,老员工多年来对某家公司或某个领域的了解可能反而成为阻碍。从公司的角度来看,年轻人的弹性让他们更倾向于接受冒险,也更愿意立即服从指挥。然而,这条强有力的信息不仅指出了权力的偏见,对员工而言更具有个人层面的意义。

砸烂办公室的梗来自《上班一条虫》。(图/《上班一条虫》剧照)
忧虑
当瑞科跟我谈到他的工程师技能已遭侵蚀时,他让我意识到了这一点。在飞机上时,我曾对瑞科说,我感觉每次写作都仿佛在从头开始;无论我曾经出版多少本书,我都没有感到信心变得更足。年轻、稳重又精力充沛的他表示理解并回答说,他身为工程师也经常感到“过气”。他担心自己的技能由内至外都在走下坡路,他表示,作为一名工程师,他现在“只是个旁观者”。
乍一听,这话仿佛完全是无稽之谈。瑞科给我的解释是,他在学校获得的科学知识不再尖端;他虽然了解新兴的信息技术领域有什么发展,但他已不能走在这个领域的前沿。那些二十出头的年轻工程师会认为,他这样三十多岁的人已经逐渐失去光彩。我问瑞科是否想过回到大学“回炉重造”,他冷冷地看着我:“我们说的可不是学会按一套新按钮那么简单。我太老了,没法再重新开始了。”
根据瑞科的说法,他这行的复杂技能已不再像是做加法,人们不能在同一基础上层层提高;新领域要取得发展,需要从一开始就采用全新的方法,而这往往是入行新人去学习才最有效率。

《社交网络》讲述了马克·扎克伯格创办Facebook的故事。(图/《社交网络》剧照)
一位欧美工程师的饭碗如果被薪酬更低的印度同行抢走,那么他就相当于被剥夺了技能——这就是社会学家所说的“去技术化”(deskilling) 的一种情况。没有谁夺走瑞科的工程知识,他的恐惧对应的是面对时间流逝时内心深处的一种脆弱感。他说,他在阅读技术方面的期刊时常常感到愤怒,“我偶然看到一些事情,我对自己说,‘我早就应该想到这些’。但我却完全没想到”。
而且,他几乎不符合“朽木”的刻板印象,但他却几乎同样确信自己在技术能力方面已经“走下坡路”。这样一来,他便把社会对年轻的强调和他个人对衰老的理解结合起来。而社会偏见更是加深了他内心对失去能力的恐惧。
瑞科在工作场合也看到这两方面的结合。他的咨询公司雇用了三位年轻工程师。他们前途无量,比瑞科年轻10岁。“我的主要问题就是怎样留住他们。”事实上,他确信那些掌握最先进技术的人终将弃他而去——“那些有能力跳槽的人,一有机会就会走人。”即使瑞科真的愿意在公司给他们话语权,这些忠诚度不高的年轻高手依然倾向于换工作。他觉得自己对此无能为力。“我管不住他们,你懂吗?”他的经验未必能赢得他们的尊重。

《黑客军团》的主角是一名网络安全工程师。(图/《黑客军团》剧照)
弹性企业的实践及英美当前政府的劳工政策,全都基于这样一条假设:技能飞速变化是常态。事实上,历史上那些拥有“旧”技能的人被淘汰出局,通常是一个缓慢发生的过程。例如,在18世纪末期,编织这样的手工技能需要经过两代人的时间才被取代。而在20世纪初,福特公司位于高地公园的工厂里的技术变革需要花费近三十年时间。
还有一个现象也许会令人惊讶,在如今许多制造业和办公室工作中,技术变革仍只是迈着相对悠闲的步伐;许多工业社会学家观察到,企业摄入新技术之后,需要很长时间来消化。发展新技能同样也需要时间,那些只读过一本木工指南的人,根本算不上木匠。
其实,每个人对时间的焦虑都与新资本主义深深交织。《纽约时报》有一位作者最近宣称:“对工作的忧虑已让我们四面受敌,冲淡自我价值,分散家庭,让社群四分五裂,工作场所的人际关系也被改变。”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话是胡说八道,新自由主义秩序能够创造就业机会,这一事实似乎已说明这种观点的虚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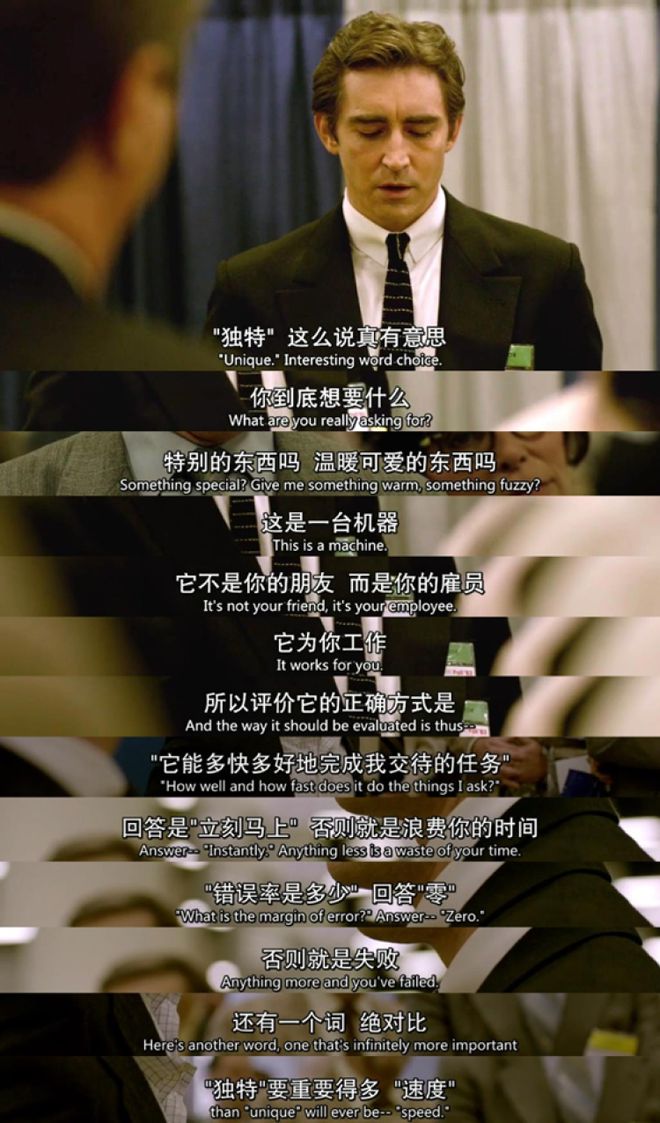
《奔腾年代》截图。
然而,这位作者使用“忧虑”一词是非常准确的。“忧虑”是为可能发生的事情而感到焦虑;“忧虑”从一种强调持续冒险的大环境中产生,当既往经验似乎无法为当下情况提供指导,“忧虑”便会增加。
如果仅仅因为外界强加的偏见而否定经验,那么在崇尚年轻的公司中,我们这些中年人就会沦为牺牲品。但是,对于时间的忧虑却更是我们身上的深深烙印。逝去的岁月似平已经把我们掏空。我们仿佛羞于提起自己的经验。这种信条会让我们的自我价值感岌岌可危,即使我们决定放手一搏也徒劳无益,因为岁月的流逝无可避免。
作者丨理查德·桑内特
编辑丨谭山山
校对丨杨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