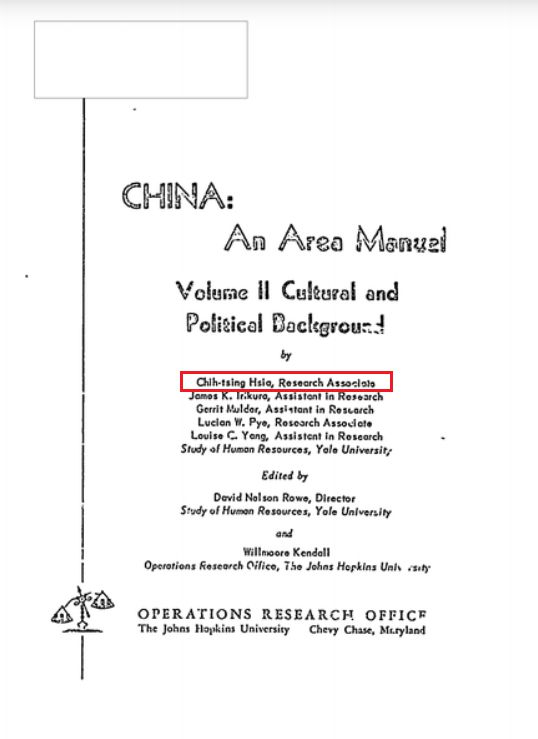
导读:2023年9月11日,中国国家安全部曝光了一起惊人的间谍案件,美国“功勋”间谍梁成运在中国落网。他不仅窃取了大量机密信息,还被伪造成“爱国慈善家”,最终以间谍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财产五十万元,终结了他长达30多年的美国间谍生涯。 很多人讶异于和平年代,间谍竟然就在我们身边。实际上,早在今年7月21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出席在阿斯彭安全论坛时就曾公开表示,已经重建了在中国的情报网络。 相比较隐秘的情报网络,对我们而言,更直观的感受是,美国政学产媒各界对中国的有组织抹黑,对中国内部进行渗透和破坏,试图阻碍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尤其是民主党上台后,致力于开展对华价值观外交,十分热衷于把中国打造为人类主流价值观的异类。其抹黑程度之恶劣,竟连美国的反华学者都抱怨,华盛顿容不得一句真话。 这倒令我想起了六七十年前的一段往事。看完这段往事,会令人感到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
2023年9月11日,中国国家安全部曝光了一起惊人的间谍案件,美国“功勋”间谍梁成运在中国落网。他不仅窃取了大量机密信息,还被伪造成“爱国慈善家”,最终以间谍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财产五十万元,终结了他长达30多年的美国间谍生涯。
很多人讶异于和平年代,间谍竟然就在我们身边。实际上,早在今年7月21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出席在阿斯彭安全论坛时就曾公开表示,已经重建了在中国的情报网络。
相比较隐秘的情报网络,对我们而言,更直观的感受是,美国政学产媒各界对中国的有组织抹黑,对中国内部进行渗透和破坏,试图阻碍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尤其是民主党上台后,致力于开展对华价值观外交,十分热衷于把中国打造为人类主流价值观的异类。其抹黑程度之恶劣,竟连美国的反华学者都抱怨,华盛顿容不得一句真话。
这倒令我想起了六七十年前的一段往事。看完这段往事,会令人感到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
【文/傅正】
美国人素来“不关心外面的世界”,事实上,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他们对于东亚的情况仍然是一片懵懂的。1941年12月9日,也就是珍珠港事件的两天以后,《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鼓励美国人民,“我们决不是孤立的”,因为“我们有像中国那样忠诚的盟友,它有着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有了这些盟友,我们就会找到太平洋战略的钥匙”。
这与其说反映了美国舆论对于中国多么友好,倒不如说反映了美国舆论对于亚洲多么无知:我们美国人现在必须要跟日本人战斗,但日本是个怎样的国家?不知道;日本军队会怎么打仗?不知道;美国有哪些优势?还是不知道。在这一刻,中国的地位就凸显了出来。中国与日本已经进行了好几年的战争,我们美国可以通过中国获得对于日本的足够多的情报。
事实上,美国人对于中国的了解更加欠缺。赛珍珠的小说几乎是一般美国民众了解中国的唯一渠道。1937年,好莱坞把小说《大地》拍摄成了电影。这部电影讴歌了中国农民的勤劳质朴。
为了拍摄影片,制作方甚至远赴中国收集服装道具,还从中国运来了两头水牛。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够轻易看出,电影对于中国农民的描绘仍然充斥着美国人的想象。勤劳、善良、吃苦耐劳,但十分贫穷,这可能就是当时美国公众对于中国人的所有印象。
按理说,这个印象并不坏,然而它却可能遭到利用。国际关系学家米尔斯海默在评价以色列游说集团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时,曾指出:
即便是那些相对较小的团体,如果它们强烈地关注某一特定议题,而其他人对此不是很关心,那么它们也能够对政策过程施加重大的影响。
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中美关系上。直到越南形势恶化时,普通美国人都不关心中国。1964年的一份评估报告显示,1501名受访者,有四分之一不知道中国的执政党是谁。
因为无知,才会上当,因为漠不关心,才会遭到利用。美国公众对于中国的无知给了少数人机会,让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刻画和涂抹中国的形象。半个世纪以前如此,今天亦复如是。
这个故事的主角有两个:一个是“院外援华集团”,还有一个是“红色中国院外集团”。两者的名字比较接近,却相互对立,它们最大的区别是前者切实存在,后者却完全是虚构的。
“院外援华集团”起源于二战时期的“亲华”游说团体。其实这不是一个固定的组织,它的人员遍及美国的政学产媒各界。比如强硬“亲蒋”议员周以德(Walter Judd)、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约翰·斯帕克曼(John Sparkman)、众议院发言人约翰·麦克马克(John W. McCormark)、参议院远东分委会主席亚历山大·史密斯(H. Alexander Smith)、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共和党参议员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这个福特后来立场有所变化,1974年接替辞职的尼克松,成为了美国第38任总统。
这些人之间的关系是比较松散的,他们之所以能够凝聚为一股势力,依靠的是蒋介石政权为纽带。
其实更引人注目的是学术界和媒体界的人,因为相较于这些议员,学者和记者可以打着“中国通”或“中国问题”专家的旗号行走江湖。有一个亲台反华组织叫作“美亚教育交流协会”,其领军人物是耶鲁大学教授饶大卫(David N. Rowe),骨干成员有吴克(Richard L. Walker)、魏特夫、威廉·麦戈文等人,后来拉进来了一些所谓的中国人,比如夏志清、吴元黎之流。在这一长串名单当中,我们姑且主要记住饶大卫这个人。
正是在饶大卫等人的策划或者推动之下,一个所谓的“红色中国院外集团”就这样被塑造出来了,而所谓“红色中国院外集团”的主要成员,其实只是美国国内那些较为理智和更有远见的亚洲问题专家。
是的,这既是一个美国反华集团各种抹黑新中国的故事,又是一个美国人自己恶搞自己的故事。在这个故事当中,您能够看到那些美式反共魔怔人的作派和风格,这样的风格延续到了今天。
坠入魔怔
美国人对于中国态度的分裂起源于太平洋战争时期。随着中美合作的深入,美国人对于蒋介石政权的态度变得复杂起来。这样高度腐败的政权是不是一个可靠的盟友?它能不能在战后掌握中国的局势?这些问题变得越来越难以回避。
从1943年开始,美国逐渐形成了一股对于重庆方面批判的声音,包括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克拉伦斯·高斯(Clarence E Gauss)、中国战区总参谋长史迪威及其顾问班子、太平洋国际学会的部分中国问题专家,以及来华的进步记者和作家。
比如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毕恩来,他的英文原名是托马斯·亚瑟·毕森(Thomas Arthur Bisson),有本书被翻译过来的书《1937,延安对话》,大家可以找来看一看。1943年7月,毕恩来在太平洋学会的刊物《远东观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比延安和重庆。他告诫美国政府,不要把宝押在蒋介石身上。重庆方面极其不得人心,未来中国的领导权很可能会转移到国民党以外的进步力量手中。谁是进步力量呢?毕恩来给出了他的答案,延安作风清廉,行政高校,深受群众拥护。与延安接触,应当成为美国政府的选项。
没过多久,1943年底,驻华大使高斯也提醒美国政府,国民党政权现在虚弱不堪,很可能不久以后会发生灾难性崩溃。不幸的是,高斯的担忧很快就变成了现实。1944年的豫湘桂大溃败让美国政界对于国民党的能力产生了巨大的怀疑。尤其是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分裂,使得更多的人转而批判国民党政权。
一场围绕蒋介石政权的政策分裂和斗争,悄然浮现。正如浙江大学历史系的张扬教授所言:“在某种程度上,亚洲冷战的序幕从对华政策大辩论时已经开启了。”
这场政策斗争的第一批牺牲品是几位中国问题专家,代表人物是三位叫作约翰的人,分别是约翰·帕顿·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约翰·谢伟思(John S.Service)和约翰·卡特·文森特(John Carter Vincent,文森特的中文名叫范宣德)。后来美国右派又加上了一个约翰——约翰·金·费尔班克(John King Fairbank),他有个更为我们熟知的名字——费正清。
这四个约翰都建议美国政府不要把宝全押在国民党头上。后来麦卡锡主义因此攻击他们,“四个约翰使美国丢掉了中国。”对此,费正清戏谑道,真正使美国丢掉中国的是另一个约翰——John(蒋)介石。
1944年4月12日,谢伟思在赫尔利的排挤下,黯然回到美国。正好在这一天,罗斯福总统突然逝世,形势急转直下。
不到两个月后,1945年6月6日,谢伟思与其他五人被捕,罪名是“涉嫌阴谋违反间谍活动法”。美国媒体指责谢伟思和伊曼纽尔·拉森(Emanuel Larsen)将绝密文件泄露给了《美亚》(Amerasia)杂志,为的是反对新任驻华大使赫尔利,并迫使美国对我党做出更加有利的外交决策。除了谢伟思以外,还有拉铁摩尔等一批学者卷入其中。这就是著名的“《美亚》间谍案”。
“《美亚》间谍案”是美国政治急剧右转的信号,也是美国与我党关系的重要转折点。
事实上,谢伟思被召回国内之初,我党还认为他是回国汇报工作去的,还期待能与美国在对日作战中展开合作。1945年4月,毛主席在中共七大上发表《论联合政府》,其中还强调,英国、美国和苏联是三个伟大的民主国家,能够始终保持团结一致。(后来的版本对此做了删改。)
两个月后,《美亚》间谍案的消息传来。6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报道了谢伟思被捕的消息,《解放日报》在社论中警告说,如果美国当局选择支持反动派,那么它必将从中国人民那里得到教训。
直到这时,美国还有一些公正的声音。1947年,左翼作家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出版了《革命尚未成功》(Unfinished Revolution in China)一书,深刻揭露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并高度赞扬了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又如费正清一再提醒美国当政者,“中共运动的力量掌握在中国人手里”,也就是说,我党绝非莫斯科的傀儡。
然而这些符合实际的判断已经无法影响美国外交决策了。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另一种声音,比如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1949年上任之初就叫嚣道,“北平政权或许是俄国的殖民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斯拉夫的满洲国。”
滑稽的是,在“没有最右,只有更右”的极端风潮下,不久以后,包括腊斯克在内的国务院官员居然遭到了美国右派连番攻击!互开右籍了属于是。
1950年2月9日,林肯诞辰纪念日,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在西弗吉尼亚的共和党妇女俱乐部发表了一场演讲,他在演讲中宣称,“我手里有一份205人的名单”,“他们全是共产党的间谍”,“对此国务卿艾奇逊完全知情,但他仍然任命这些人起草外交政策”。这份演讲一经公布,舆论哗然!这一天就成为了麦卡锡主义开始的日子。
一时间,各种阴谋论甚嚣尘上,弥漫在美国的大街小巷。1953年,朝鲜停战。按照协议,“自由”遣返,有21名美军战俘拒绝回到美国。对此,美国参众两院和新闻媒体借机大肆炒作“朝鲜战俘事件”。按照他们的逻辑,问题不仅仅是21个人拒绝回国,而是那些回国的战俘当中有多少人受到了共产主义的“洗脑”,而自觉地成为了红色中国的间谍?
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有超过2300名美军战俘接受了中国指派的任务,他们回到美国国内,随时准备利用各个机会传播共产主义观念。美国舆论纷纷哀叹:“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这么多的被俘士兵最终通牒。”
按照美国新闻媒体和大中小学等意识形态机构的套路,共产党人善于使用一种神秘的精神控制术,能够把人们变成一件件为其服务的冰冷工具。现在他们已经成功把热爱和平的中国人变成了统一着装、训练有素的军队。接下来,这个“共产主义怪物”将要把它的触角伸向世界的各个角落。
不用奇怪,类似的套路直到今天,仍然频繁地出现在美国影视剧和电脑游戏当中。无知愚笨、对外部世界极端无知,却总是自以为是的美国公众,恰恰为这些阴谋论提供了最好的土壤。
尽管麦卡锡本人在1954年底遭到了弹劾,并在1957年5月2日死于急性肝炎,但红色中国的阴谋论并没有因此而退潮。
除了恶搞自己人以外,美国人也恶搞了中国。
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军方曾组织编纂过一部《中国:地区导览》(China: An Area Manual)手册,供参战美军使用。其中“文学”“思想”“大众传播”三大章,以及其他若干小节交给了一个叫作夏志清的美籍华人撰写。在美国情报机构和新闻机构的支持下,夏志清后来把文学的部分加以扩充,撰写成《中国现代小说史》,于1961年3月出版。
为了对抗由鲁迅、茅盾等人构成的左翼作家谱系,夏志清刻意夸大和吹捧了张爱玲。直到今天,此人的文学史仍然在国内备受吹捧。
事实上,就连张爱玲本人都沦为了美国冷战的工具。她后来承认,美国新闻处给她拟定好了故事梗概和提纲框架,指使她往里头填小说。这部小说名叫《赤地之恋》,出版于1954年,它对于后来什么《软埋》之类书具有开创性的作用。
与粗俗弱智的阴谋论不同,上述系统性的抹黑都是以某种“专业”或“中立”的面貌出现的。
康奈尔大学人类学家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到东南亚考察后,得出结论:东南亚的华人群体并非共产主义者,但他们都希望一个强大的中国能够给予他们保护和荣耀。中国大陆显然是强有力的。为此,施坚雅建议美国政府赶紧大力打造蒋介石政权的民族主义特性,以便把东南亚华人吸引过去。
他的报告很快得到了美国国务院和新闻署的重视,成为了美国对东南亚华侨的心理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个过程当中,香港,这个华人文化辐射东南亚的桥头堡,得到了特殊的重视。关于这个问题,我以后再讲。
总之,麦卡锡主义时代是美国有组织系统化抹黑中国的开始,也是他们内部整肃,把任何对中国持有公正态度的人打为间谍或通共分子的一次高潮。
麦卡锡死了,但美国人互贴标签的闹剧才刚刚拉开了帷幕。

《中国:地区导览》第二卷(饶大卫编)扉页的作者名单,夏志清排在第一个
虚空索敌
很显然,没有“院外援华集团”的推波助澜,麦卡锡主义的风潮不可能挂得如此猛烈。这股风潮刮遍了美国知识界、文艺界,但它主要的针对对象还是艾奇逊领导的国务院。
其实艾奇逊也挺倒霉的,一方面,我们《别了,司徒雷登》中痛骂艾奇逊亲蒋反共,“在这里强奸了美国的民意”;另一方面,麦卡锡主义却攻击艾奇逊有意放纵亲共分子,出卖盟友蒋介石。
总之,蒋介石集团借助麦卡锡主义干扰美国外交,这引发了美国国务院的强烈不满。1950年,助理国务卿腊斯克当着台湾政客蒋梦麟的面,指责蒋介石政府试图绕过美国国务院,利用“院外援华集团”干预美国外交决策。国务卿艾奇逊甚至建议杜鲁门总统赶紧对“院外援华集团”展开调查。
1952年,美国《记者》杂志刊文揭露这个服务于蒋介石政权的“院外援华集团”。《记者》杂志指出,“院外援华集团”有个致命的武器,简单而有效,就是逼人站队:你不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是吧?那你就是莫斯科的走狗。任何美国人,无论他是官员还是平民,只要他不赞同蒋介石,他就有可能被扣上“赤色分子”的帽子。
这些曝光当然令“院外援华集团”十分恐惧和痛恨,怎么办?行,既然你说我是蒋介石的工具,那么我就说你是共产党的间谍。攻击我的人越多,就说明红色中国在美国的特洛伊木马越强大。
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这给美国的震动非常大,第二年,也就是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防教育法》。在这个背景下,美国人开始了新一轮抓“共产主义间谍”的运动。
又过了一年,1959年,美国《水星》杂志发表文章,提出在美国有一股干预其决策的隐秘力量——“红色中国院外集团”。它的成员包括大批政学要员,比如“对外政策协会主席”塞立格曼,此人1958年曾公开建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又如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罗勃特·阿莫莱、杜勒斯的前政策顾问罗勃特·波威,以及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大批中国问题专家,因为他们被指控为对红色中国采取“绥靖政策”。
再比如,高级研究机构“美国人大会”的60名专家,因为他们曾联名上书1954年的联合国大会,要求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
除此之外,还有12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有幸上榜,他们在1958年10月联名要求联合国托管台湾。
在《水星》杂志的渲染下,这些人通通都是为红色中国安插在美国的特洛伊木马,目的是改变美国的外交方向,使美国迎合红色中国的利益。
然而事实上,上述所有人跟中国都没有关系,他们大多持有“两个中国”的主张。
也就是说,在所谓“红色中国威胁”的恐慌氛围之下,美国人开始了一场“互开右籍”的运动,而以“亲蒋反共”为首要目标的“院外援华集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60年,美国学者罗斯·凯恩(Ross Y. Koen)撰写了《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The China Lobby in American Politics)一书,准备由麦克米伦公司(Macmillan)出版。
这本书揭露了台湾蒋介石政权深度介入美国外交决策的内幕,揭露了“院外援华集团”如何制造舆论,打击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并左右美国外交决策的真相。
毫无疑问,蒋介石政权及其在美国的代理人——是的,你没听错,“院外援华集团”真是蒋介石的代理人,他们似乎更在乎蒋介石的利益而不是美国的利益——对于这本书是非常惊恐的。
该书还在预审阶段时,“院外援华集团”和蒋政权在美的“外交人员”就获悉了大体情况。他们立即采取行动,竭力阻挠该书出版。台湾的所谓“驻美大使馆”甚至宣称要起诉出版商麦克米伦公司。
正是在蒋介石集团和“院外援华集团”共同压力之下,罗斯·凯恩的著作没能正式出版发行,仅有少量样书存留在出版商和图书馆的书架上。
这件事让蒋介石集团和“院外援华集团”意识到,他们已经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反感。仅仅阻挠罗斯·凯恩的著作出版就够了吗?远远不够,就算这次拦住了罗斯·凯恩和麦克米伦出版公司,还会有下一个罗斯·凯恩和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站出来揭露他们。怎么办?那就只有主动出击了。
为了对冲罗斯·凯恩的影响,“院外援华集团”决定塑造一个更大的敌人,通过这个敌人再次制造恐慌氛围,“红色院外集团”就是一个好的抓手。
在蒋介石政权的配合下,“院外援华集团”炮制了一本著作,题为《红色中国的院外集团》(The Red China Lobby),于1963年出版。从标题也能看出,这本书大肆渲染,美国已经遭到了“红色中国”的全方位渗透。它的核心观点有四个:
第一,除了台湾和澎湖列岛,中国已经被一个外来的政权所占领;
第二,莫斯科—北京轴心(Moscow-Peking Axis)已经发动了针对“自由世界”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与前两次世界大战不同,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仅仅停留在军事领域,它是一场波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综合战争;
第三,“红色中国”的意图是控制除了苏联帝国以外的所有亚洲地区;
第四,莫斯科—北京轴心的终极目标就是孤立并打败“自由世界”的领袖美国。
第五,为了战胜对手,保卫所谓的“自由世界”,美国有必要开展一场整肃运动。首要的整肃对象就是其国内的“红色中国院外集团”。
为此,这本书提出了大概两条鉴别“红色中国院外集团分子”的标准:
(1)凡是提出离间“中苏关系”或倡导“与中国接触”的人,都是潜在的红色中国特洛伊木马。比如前国务卿艾奇逊主张过美国应该离间中苏关系,比如著名学者费正清就是这项政策的积极鼓吹者,那么他们都是“红色中国”在美国的代理人。
(2)凡是认为中国持有和平主义立场的人,都是潜在的红色中国特洛伊木马。美国学者洛德·林赛(Lord Lindsay)和华尔特·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都认为中国不太可能大规模使用武力,中国会采取和平共处的立场。这些人也是“红色中国院外集团”的成员。
总之,“红色中国院外集团”实力雄厚,规模庞大,包括不仅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弗吉尼亚大学等多所顶尖名校的大批专家,更包括康奈尔大学校长迪恩·马洛特(Deane W. Malott)和罗切斯特大学校长科尼利斯(Cornelis W. de Kiewiet)这两位大学校长!
这份名单几乎把所有反对无脑吹捧蒋介石的亚洲问题专家统统一网打尽了。显然,“院外援华集团”及其支持者蒋介石政权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们希望编造一个庞大的阴谋论,让任何理智的人都缄默不语。只要美国越癫狂越意识形态上脑,蒋介石集团和他的美国朋友就越有机会火中取栗。
然而在这本书出版的1963年,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分歧已经很明显了。随着中苏矛盾愈演愈烈,美国国内要求重新评估中美关系的呼声越来越高。
1966年,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了中国问题听证会,也称为“富布莱特听证会”。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参加了这场听证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是时候调整对华政策了,即现在应该对中国采取一种“遏制但不孤立”的政策。也就是说,美国在保持军事遏制中国大陆的同时,也尝试接触中国大陆。
“富布莱特听证会”让“院外援华集团”陷入了一场更大的恐慌。他们意识到,中美接触的大门一旦打开,他们的谎言和神话将会被彻底戳破,美国将要抛弃他们。
因此听证会结束后不久,“院外援华集团”修改和再版了《红色中国的院外集团》一书。新版改名为《“新”红色中国院外集团》(The “New” Red China Lobby),尽可能地扩大了打击面。
例如亚洲协会(Asia Society)、亚洲研究协会、美国人考察远东政策协会(Americans for a Review Far Eastern Policy)、全国教会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服装业联合工会(Amalgamated Clothing Workers)、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等学术机构和民间团体,连同《纽约时报》等媒体,居然一口气都成为了红色中国的院外集团。我们这么牛逼我们怎么不知道?!
显然,“院外援华集团”期待新一轮的麦卡锡主义运动。在他们的渲染下,美国似乎已经不是美国人的美国了,真正掌握美国的是一个由红色中国控制的“deep State”。这类话术多么令人熟悉!多少年过去了,他们一点都没变!
很狗血是吧?更狗血的还在后面。1968年,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他在竞选中承诺,要在任内解决越南战争的问题。怎么解决?你不试图改变与中国的关系,越南问题没法解决。
所以在尼克松胜选后不久,1968年11月6日,一批东亚及中国研究专家就通过亨利·基辛格向尼克松递交了一份备忘录,他们包括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孔杰荣(Jerome Cohen)、赖肖尔、史华慈、傅高义,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鲍大可和麻省理工学院学院教授白鲁恂等人。这份备忘录也被称为《费正清备忘录》(The Fairbank Memorandum)。
确实,这些真正研究中国的专业人士被“院外援华集团”和右翼分子压抑得太久了,尼克松的当选成为了改变这一切的契机。
《费正清备忘录》对尼克松政府后来调整对华政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备忘录指出:
(1)迄今为止美国的对华政策是错误的,它建立在“修辞”(Rhetoric)而非“现实”(Reality)的基础之上。
(2)美国总统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改变过去的错误,缓和与中国的紧张关系。比如减少周边世界对中国的敌意,比如通过接触给中国领导层提供不一样的选项,再比如可以使当前和未来的中国领导人对于过去的世界观产生疑问。
(3)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建议中美高层领导人举行秘密会谈,建议将越南问题会谈作为将中国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的一部分,建议修改针对中国的反弹道导弹(ABM)部署计划,减少对中国的贸易制裁,等等。
应该强调,参与备忘录署名的中国专家绝不是对华友好人士,他们都是完全站在美国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的。但毫无疑问,他们都是专业的,这份备忘录预言了后来中美关系的走向。只不过备忘录建议的“中美高层领导人秘密会谈”,变成了基辛格的秘密访华,并取得了重大成功。
“院外援华集团”很快获悉了《费正清备忘录》的大体内容,更加惊恐。他们意识到过去对于学术界的打击还不够,于是再一次扩大了“红色中国院外集团”的名单。
“院外援华集团”的骨干分子、美亚教育交流协会主席饶大卫,亲自下场操刀。他与右翼刊物《国民评论》共同制定了一个打击计划,由饶大卫出面草拟写作提纲。
在饶大卫的笔下,“红色中国院外集团”又双叒叕扩大了。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统统成为了“红色中国”的秘密阵地。
此外还包括了一堆民间团体,比如世界事务理事会(World Affairs Councils)、女性选民联盟(League of Women Voters)、校际联合国协会(Intercollegiate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联合国协会、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Americans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等等。
这些都是NGO哈。除了上述NGO以外,“院外援华集团”还把攻击目标盯上了美国的所有电视媒体。为什么呢?1960年代正好是美国电视媒体兴起的时候,电视媒体对于青年学生反越战运动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一定得是被红色中国策反了呀,被红色中国策反了呀。
所以你看,这就是美式魔怔人的典型操作。
根据这份提纲和名单,“院外援华集团”又炮制了一本著作《红色中国及其在美国的朋友:一份关于“红色中国院外集团”》。饶大卫先后找了几个人写作,都不满意,索性自己动手编造。
在这本书当中,他总结了“红色中国院外集团”的思想特征:凡是那些宣称“国民党政权腐败”“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失败不可避免”“美国不能被国民党牵着鼻子走”“美国应该主动缓和与中国的关系”的人,统统都是“红色中国”的代理人,或者被“红色中国”蛊惑的人。
这本书最终在1971年出版,台湾当局立马就把它翻译成了中文,取名《中共在美游说内幕:美国支持世界自由协会报告书》,后来又多次在台重印。
显然,仅仅虚空索敌,捏造一个不存在的对手还是不够的。“院外援华集团”还需要给对手编造一个罪名,而且这个罪名必须是普通美国公众深恶痛绝的。于是一个巨大的谣言开始发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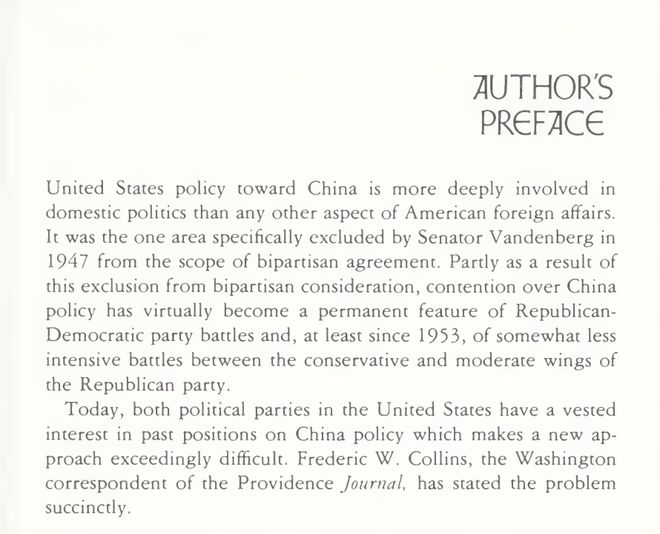
罗斯·凯恩在著作的序言里指出,美国对华政策比其它外交政策更加深入地卷入了国内政治,关于中国的争论已经成为民主、共和两党斗争的持久特征。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
陈年老谣
这个谣言起源于朝鲜战争时期。原本从未关注过中国,也根本不了解中国的美国联邦麻醉品局(Federal Bureau of Narcotics)突然针对中国提出指控,宣称中国正在国际黑市上大量出售鸦片和海洛因,以此牟利来维持在朝鲜的军队。联邦麻醉局雇员安斯林格(Harry Anslinger)多次在美国国会和联合国大会上,出面指证“红色中国”的“毒品计划”。
在麦卡锡主义的压力下,没有任何人胆敢要求联邦麻醉局或安斯林格个人提供具体的证据。“中国正在密谋组织一个全球毒品网络”这种荒诞的谣言居然被“重复千遍”,渲染成为了不容置疑的事实。
包括《时代》周刊在内的著名媒体,纷纷出台标题为“中国正在用海量毒品侵蚀美国”的文章。“红色中国”“毒品”这两个形象关联在一起,所谓“莫斯科—北京”轴心正在密谋操纵世界的说法似乎更加有鼻子有眼了。
按照美国联邦麻醉品局的说法,中共将数量庞大的毒品走私到越南,再通过其在越南的贩毒网络分销往世界各地。越南共产党既是中国贩毒的工具,也是中国使用贩毒收益资助的对象。
为了掌握“中国政府有组织贩毒”的具体情况,195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还真的派人去越南进行了专门调查。调查的结论是,这项指控纯属莫须有,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存在这样的贩毒网络,恰恰相反,中国政府对毒品行业采取非常严厉的禁止的态度。
中情局的报告同时指出,在中国云南边境确实有少量毒品流出,但这应该是云南当地少数民族村寨所为,并没有得到中国政府任何支持。
然而美国当局在各种舆论和政治压力之下,根本不敢把报告的结论公之于众,相反,报告被打上“绝密”的标签,束之高阁。这件事情证明了,美国人所为的“调查真相”在政治需求面前一文不值。任何不利于把“红色中国”妖魔化的材料都将被自动过滤或者忽略。
后来的事实证明,云南边境毒品恰恰是残留在那里的国民党军队制造的,而且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完全知道这件事情!
刚才提到罗斯·凯恩在1960年的《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一书。这本书就披露了蒋介石政权与东南亚毒品贸易的关系。
可以想见,台湾当局知道这本书后,是多么惊恐和愤怒!这也成为了它煽动美国“院外援华集团”绞杀凯恩著作的重要原因。
凯恩的著作还没出版,美国官方就赶紧出面为蒋介石政权背书。于是,罗斯·凯恩对于“红色中国贩毒网络”的辟谣反而在政治压力下,不幸成为了“谣言”。
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美国政府默许和纵容了国民党军队的贩毒行为,也变相地默许和纵容了毒品在美国的销售!
进入60年代,对华理智的呼声越来越高。为了扭转逐渐不利的局面,为了进一步打击美国的理智派,也为了进一步服务蒋介石政权,“院外援华集团”决定抓住毒品问题大做文章。几年以后,饶大卫在给同事的信中,恬不知耻地说道,就美国公众而言,妨害中美关系缓和的关键因素就是中国的“毒品走私问题”,它是“红色中国院外集团”的“阿喀琉斯之踵”。
从策略上来讲,饶大卫是正确的。60年代,美国青年反主流运动兴起,毒品问题成为了全社会的焦点,只有将毒品与“红色中国”深度绑定,才能激起美国普通民众的反华情绪,把彻底否定所谓“红色中国院外集团”的合法性。
在饶大卫、崔戈等人的策划和帮助下,堪德林(A. H. Stanton Candlin)炮制了《心理化学战:中共对西方的毒品进攻》(Psycho-Chemical Warfare, The Chinese Communist Drug Offensive against the West)一书,并于1973年在保守派出版公司阿灵顿屋(Arlington House)出版。那个时候,中美关系已经拉开了正常化的序幕。
我们应该明白,与美国人打交道,绝不能抱有一种功利的态度,不能因为我们跟美国关系缓和了、好转了,就忘掉了两国在性质上的根本不同。事实上,哪怕是中美关系最好的时候,美国人也从来没有一刻放松过在价值观上彻底否定我们。
请注意,《心理化学战》出版的时间是1973年,早在六年前,1967年,国民党残军与坤沙民兵武装在老挝北部爆发激烈冲突,双方各有数百人伤亡。有美国学者将其称为“1967年的鸦片战争”(The 1967 Opium War)。
这个事件使得“金三角”的真相曝光,根据后来的揭秘文件,参与毒品制作和贩卖的势力不仅有国民党、东南亚商人和当地割据军阀,还有中央情报局。总之,这下美国政府很难再给蒋介石政权捂盖子了。
更加滑稽的是,当时中苏关系十分紧张,莫斯科居然捡起了美国人和国民党玩剩下的老谣言,开动官方机构,大规模宣传中国大陆正在用鸦片毒化“自由世界”!
中央情报局在1972年的一份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关于中国输出毒品的舆论基本来自莫斯科和台湾。也就是说,极端反苏反共的“院外援华集团”现在居然在帮俄国人的忙!
我相信,莫斯科出面造谣,这也是“红色中国毒品网络”这个谣言在美国消停下来的重要原因。
在《心理化学战》出版的第二年,1974年,罗斯·凯恩的著作《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终于得以出版发行,其中关于国民党政权走私毒品的描述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
可以说,这是一个标志,服务于蒋介石政权的“院外援华集团”走向了边缘。然而我们无需乐观,类似的组织从来没有因此而停止过它的活动。他们只是变换了马甲。

堪德林在《化学心理战》一书中虚构的“红色中国”向金三角贩卖毒品路线
变换马甲
1966年,美中关系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成立。这个机构由来自学界、商界、媒体界、宗教界等60余名人士组成。背后得到了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大力支持。
美中关系委员会的主要定位就是重新评估中美关系。它成立的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就公开声明表示欢迎,希望它能够站在“客观性”“分析性”高度,向美国公众介绍“红色中国”的情况。美国务院表示,对于红色中国的政策“必须进行不断的研究和考察”。
很显然,美国外交部门不是傻子,他们也意识到过去“院外援华集团”完全站在蒋介石政权一边,给他们传递错误的消息,甚至对他们施加无端的政治压力。中苏关系的破裂已经证明了,“院外援华集团”总是在撒谎。
美中关系委员会成立以后,发挥了重大作用。举个例子,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开启了举世瞩目的“乒乓外交”。这里面就有美中关系委员会的推动。
除此之外,1969年10月成立的“对华新政策委员会”(Committee for a New China Policy)也是一个旨在推动美国当局改善对华关系的重要民间机构。这些机构利用当时蓬勃发展的电视媒体,频频出境辩论对华政策,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对此,“院外援华集团”当然不能忍啊。比如其骨干成员周以德,就利用共和党内的关系,多次试图劝说尼克松改变“与中国大陆接触”的政策,但遭到了尼克松的明确拒绝。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正式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此后,美国“院外援华集团”的部分成员,又组织成立了一个所谓的“自由中国委员会”(Committee for a Free China),通过不断渲染和打造“红色中国”与“自由中国”的对立,来维护蒋介石政权的利益。
我们注意,从这时开始,所谓“院外援华集团”的重点工作已经不再是全盘否定“红色中国”了。强化台湾地区的所谓“独立性”,成为了他们的目标。
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美国正式断绝跟台湾的官方往来。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名叫“美国在台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AIT)的所谓“民间机构”。
事实上,我们确实低估了美国“旋转门”体制的巧妙之处。类似“美国在台协会”乍看上去并不代表美国的官方意志,然而其成员完全有可能通过“旋转门”成为美国的政府官员。美国人玩了一个“把东西从左口袋放到有口袋”的把戏。
从表面上看,随着美国断绝与台湾地区的官方往来,当初的“院外援华集团”似乎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但这不代表他们不能炒作台湾议题以及其他一切反华议题。
今天美国的对华意识形态冷战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回望当年“院外援华集团”的种种奇葩行为,真是“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魔怔啊。
参考文献
陈国球:《“文学批评”与“文学科学”——夏志清与普实克的“文学史”辩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郭济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
米尔斯海默、沃尔特:《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王传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水晶:《替张爱玲补妆》,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
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3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张杨:《冷战与学术:美国的中国学1949—197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
Ross Y. Koen, The China Lobby in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
Stanton Candlin, Psycho-Chemical Warfare, The Chinese Communist Drug Offensive against the West, New Rochelle: Arlington House, 1973.
在以上著作中,本文主要内容参考的是张杨教授的《冷战与学术》,特此说明。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