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的转型期,国内青年就业问题严峻,“躺平”、“内卷”等词汇从网络到现实,充斥公共空间。清华博士土木工程师曹丰泽,放弃北京中产生活,选择去非洲修水电站的真实故事,如一股清流,在年轻人和学者中间激荡起很多思考。
世界格局深度演变,中国正通过“一带一路”等全球治理新实践,在全球舞台上积极作为。曹丰泽等中国当代青年的发展路径的选择,无疑是这场全球大变局的投射。
同样身处变革期,当下中国青年的焦虑与40年前中国转轨时期的潘晓的感叹“人生之路怎么越走越窄”有何异同;面对大变局时代和日渐多元的中国,中国青年如何自如展现丰盛张扬的自我,11月17日,《文化纵横》杂志组织了题为《全球变局时代的中国青年——从“潘晓讨论”到“清华博士去非洲”》的研讨会,邀请来自青年工作管理部门、学术机构和媒体机构的青年问题学者和研究专家,展开了讨论。观察者网也受邀参加,并推出【新青年·观】专题,关注当下青年关心的话题。
本文根据作者在会议上的发言整理,经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发布。】
曹东勃:
这一年比较特殊,疫情突然就结束了,整个社会放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又打开了,国际合作交流又重新恢复正常。
过去三年绝大多数学校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封闭管理的,现在要面向社会重新开放,放开之后大家如何适应,对青年人来讲,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认识这个新情况。
很快各种“梗”接踵而至,“孔乙己文学”、青年人的就业形势……目不暇接。

今年万圣节上海的狂欢活动,青春上海公众号在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内转发了基调不同的两篇文章:一开始是转载了《解放日报》的文章,肯定了上海是一个包容性的城市,青年人需要有宣泄的空间;但是很快又发文提醒说巨鹿路上人已经很多了,建议大家不要再前往。能够感觉到这背后有一种紧张感。
虽然这场狂欢发生在上海,但在全国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现象。以往万圣节这类洋节青年人也过,但是像今年这么过的,这是第一次。不是过成西方的样子,是把过去几年的“梗”全都高密度地堆积到一起,这是个新的现象。以往万圣节年轻人主要去欢乐谷,而今年,一场魔幻现实主义的活动被搬到了狭窄的马路上。
这一系列的事件,揭示了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青年焦虑背后,不是一代人
最近我看到一篇《当孩子的高中班主任,解散了家长群之后》的报道,有老师解散家长群之后,留言区清一色地评论说,要珍惜敢于解散家长群的老师。
我们从小到现在,没有被管得这么严格。2003年非典的时候,也有一段封控期,当时还没有大数据,没有行程码。但那个时候我们的父母(多为50后群体)对我们几乎是不闻不问,或者是隔一周打一个电话,提醒我们要多吃点东西,不要天天在寝室里打游戏。
这一代00后的家长普遍是70后,按理说见过更大的世面,但是他们对子女的干预,指导子女人生的这种“爹味”十足的状态,在某种程度上也不亚于50后、60后。他们指导得很细致,再加上现在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对子女的关怀“无微不至”。学校稍微有一点做得不到位的,压力首先是来自于家长,而不是学生,甚至双方的压力一起来。
所以,一个高度“内卷”的青年人背后,可能站着一对心态焦灼的父母,这不是一代人的内卷,还有另一代人在指导。

给青年有温度的引导和建议
青年人很多时候关注的其实都是亚文化圈的议题,如性别领域的对立,婚恋领域的不婚、独身,特别是经历过封控措施之后,使得这种思潮有比较大的市场,包括今年还出现了厌童这样的新话题……
今年上半年,就业话题被炒热是主流媒体亲自下场的后果。青年人本来探讨孔乙己文学,是一种自嘲、反讽、玩梗的态度,结果一些主流媒体过早、过严肃地将之定性为“脱不下长衫”的状态。一下子捅了马蜂窝,很快就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7月的时候,主流媒体呼吁要树立正确的就业观。这个话当然不错,但在那个当口,又被青年人攻击。其实问题在于不仅仅是改变观念这么简单,我们面临的很多严峻复杂的形势,不是观念的问题。
青年人不愿意生孩子,我们说要树立正确的生育观;不愿意结婚,我们又说要树立正确的婚姻观、恋爱观;年轻人慢就业、不就业或者申请gap year(短暂休学年),我们引导他们要树立正确的就业观。要我看,好的宣传不是针锋相对的宣传,倒不如摆事实,把道理放后面,或者说隐而不彰,体现在其中,否则就是在空讲大道理。

读懂年轻人的怕与爱、焦虑与关切
我这学期也开了一堂改革开放史的课程,虽然这是四史的标准课,但是我用了自己的一套讲法,自己设计了一套大纲。主要是讲1978-2012这段历史时期,作为对后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一个铺垫,让00后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如何一路走来。
我也谈到了潘晓来信,我搜集了学生的一些感想,他们觉得我们在今天仍然有类似潘晓同样的问题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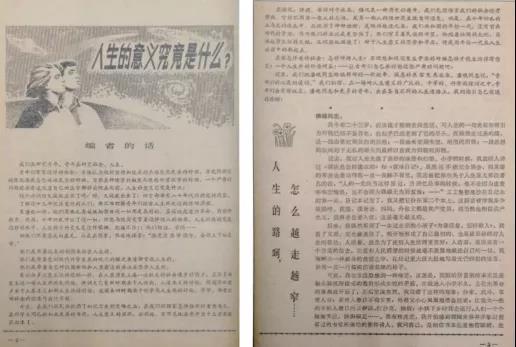
80年代初我们为什么会出现潘晓来信?从原来的社会主义突然抛入市场化转型,由保护得很好的真空地带,一下子可以允许释放自己的欲望,追求自己的需要,有多元化的选择,一下子手足无措了,价值体系一下子没了主心骨。为什么感叹人生的路越走越窄等等?我们看到当时的潘晓来信提到的很多问题,其实都是一地鸡毛的,但更多的是对选择多了之后的迷茫。
今天的青年人差不多也是如此,他们也觉得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迎接多元的世界和多种道路的选择。包括他们也提到了未来的方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更深层次的也提到了985废物的问题。所以他们热衷“发疯”。
校园封闭管理会让人的大学体验和学习状态发生很多变化。我们图书馆2023年1-6月的图书借阅量,与2019年的同期相比,总量上几乎下降了3万多本。
这当然有疫情的影响。另一方面,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结构性的变化,特别是经典读物有些变化。在疫情之前看的很多的是浪漫的东西,在疫情之后、放开之后看的多的是法学、性别话题,比如《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包括一些对于世界阴郁的、冷冰冰的理解,比如《三体》《倦怠社会》,去年还有好多去借阅《叫魂》。年轻人对社会、对世界的想象,借助于书籍选择,我们能看到,不能说更增添了几分阴郁,但至少增添了几分现实、理性冷静。
通过这些观察,我们想知道青年人到底在想什么,他们在阅读什么,在焦虑什么,这些都是和现实勾连起来的。这背后其实很值得思索。他们也谈到了书本、课堂的正能量和现实世界残酷内卷之间的脱轨。我们不能把自己关在真空中去熬制鸡汤,如果不去回应青年人的真实关切,其实鸡汤的效果是很有限的。要给年轻人营造一个多元包容的生存环境,读懂年轻人的怕与爱,焦虑与关切。

让年轻人真正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这次万圣节的狂欢活动,稳妥处理是合适的。这对于营造上海的城市形象,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是有积极意义的。现在每个城市都在为争取年轻人、争取年轻人的心、成为一个青年友好型的城市而各显其能。现在,至少这个城市允许年轻人心里有苦闷的时候可以适度“发疯”,这是温和的,也是有温度的。
如何面向当代青年,更好地处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碰撞,这一直是个难题。疫情之前,我们对年轻人过洋节的态度一直是比较谨慎的,当然有的年份还有更激烈的反对和批判,今年似乎稍微允许在合理的限度之内释放了一点天性。其实年轻人的所谓过洋节,它并不是简单的一种复制,是有现实主义取向在里面的,是有相当程度的文化主体性在里面的,里面的符号从四大名著到鲁迅,都是民族的。
过洋节难道是中外之争吗?是土与洋之争吗?是在暴露生活中需要我们去解决的实质性问题、数字化生存职场境遇中的“社畜”遭际,还是我们简单地将其定性为过洋节然后一棒子打死?
关键是我们能否读出这些符号背后的真问题,这也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追问,以及回应当下青年根本的关切。他们面临着生活当中更多这些实质性的问题,需要去解决。
我觉得我们不能刻舟求剑,否则必然是南辕北辙。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