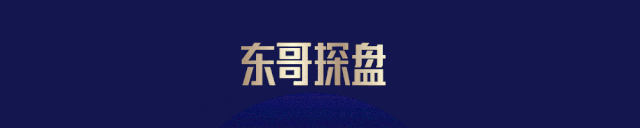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
解决的办法就是“先租后售”。
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文
2023年8月25日国常会审议通过的《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是一个对房地产乃至整个经济都可能产生重要影响的政策。目前,影响保障房政策落地主要有三大问题,第一是需求从哪里来;第二是资金从哪里来;第三是如何防止公共服务被挤兑。
从目前一些城市对符合政策的保障对象进行的抽样调查来看,有保障房需求的家庭数量还很小,即使全部得到满足,对经济的拉动也还微小。这主要是“保障对象”覆盖面还太小,大量在城市打工的临时就业者和非正规就业者都被排除在“保障对象”之外。以深圳为例,2020年深圳实际人口约2100万,约70%以租赁方式居住在城中村等非正规住宅内,如果保障房建设的规模不能足够大,就无法抵消商品房(2021年,商品房销售面积17.9亿平方米)下降对建筑、建材、家具装修等行业的冲击,保障房也就难以达到中央所要求的战略性作用。
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199万人,其中只有不足45%的人在城镇有了自有住房(而且越发达的大城市这一比例就越低),其余55%的人都是以租赁的方式在城市生活。如果仅将其中1亿户(约3亿人)纳入保障体系,按照每户保障面积50平方米计算,就会有50亿平方米的建设规模,均摊到3年,每年建设规模就高达16亿平方米以上,即使每平方米成本只有5000元,也可以拉动8万亿元投资。
需要注意的是,打工者为主的保障对象收入较低(这也是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之一),属于中国9.6亿人均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群体(家庭收入4000~6000元/月)。尽量压低保障房成本就是保障能否扩大供给规模的关键。除了压低每套的建筑面积外,控制征地拆迁成本,也是降低保障房价格最重要的因素。
紧接着的第二个因素就是资金。如果把这些打工者都纳入“保障对象”,巨大的资金从何而来?这就涉及保障房的供给模式。现在的保障房和商品房的差别主要有两条,第一是成本价,小户型;第二是封闭运行,不得上市。这两条都不太适合农民工这样特定的保障群体。
首先是一次性支付成本价,对这些打工者而言依然是不小的负担(中国月均收入小于1000元的还有9亿人),即使能够通过提高容积率把每平方米的土地成本压到5000元,加上建安成本,每平方米的成本也可能超过1万元甚至1.5万元。一套50平方米的保障房成本就是50万~75万元。
其次是打工者的流动性较大(这是新加坡这样的国家所没有的问题),如果每到一个城市就购置一套保障房,无论对家庭还是社会都是巨大浪费,这就决定了这部分打工者居住需求仍将以租赁为主。就算租金可以达到2000元/月,一年租金是2.4万元,20年是48万元。即使不考虑利息,保障房也很难收回成本。
解决的办法就是“先租后售”。还是同样的例子,把租金转为按揭,20年后保障对象已经缴交48万元,这时给其一个“房改”的机会,补缴剩余成本2万~27万元后可以获得完整的商品房产权。由于市场房价远高于保障房成本价,我们可以预判除非特殊情况,所有保障对象都会参加“房改”缴清所有尾款。当然,这可能需要建立一个不同城市保障房租金的“兑换”机制,以满足在不同城市打工者将其他城市的租金兑换到最终定居的城市。
根据以前厦门规划局和财政局所做的一个内部测试,即使考虑5.5%的利息,结果依然不变。由于有稳定的现金流且最终可以入市,保障房本身可以成为高质量的抵押品(商品房价格相对保障房成本落差越大,抵押品的质量就越高),厦门国开行曾表示愿意无限量为“先租后售”保障房提供长期贷款。这就解决了保障房最大的问题——钱从哪里来。
这个政策对现有保障房政策的一个关键突破,就是从与商品房完全隔绝封闭运行,变为有期限的封闭运行。这样做的好处:
第一是解决了高流动性、低收入就业者的保障需求。这些打工者可以把在不同城市保障房的租金转换为按揭,为在最终定居城市购房积累资本;
第二是解决了保障房和商品房市场间的套利行为,由于20年基本上是一个打工者的工作寿命,只要规定一个家庭只能购买一套,那么想通过购买保障房在商品房市场出售套利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第三是通过帮助每个家庭完成重资产投资,快速建立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每个家庭都可以通过地价上升,分享社会财富的增长,从而抑制贫富差距扩大,实现社会的稳定。
由于中国没有个人所得税、财产税这样的直接税,保障房门槛的降低会使公共服务水平高的一二线城市变得非常具有吸引力。大量人口循此途径涌入大城市、超大城市,会给这些城市的财政带来极大负担。这就需要将保障资格同就业挂钩。由于中国的税负主体来自于企业,只要一个人在城市缴纳五险一金和个人所得税,就可以认定其是合格的城市纳税者,由于城市就业是有限的,保障房与就业挂钩可以有效防止大量人口无序涌入头部城市。显然,住房保障和就业挂钩要比依靠户籍制度更能保护城市公共服务不会被大量挤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