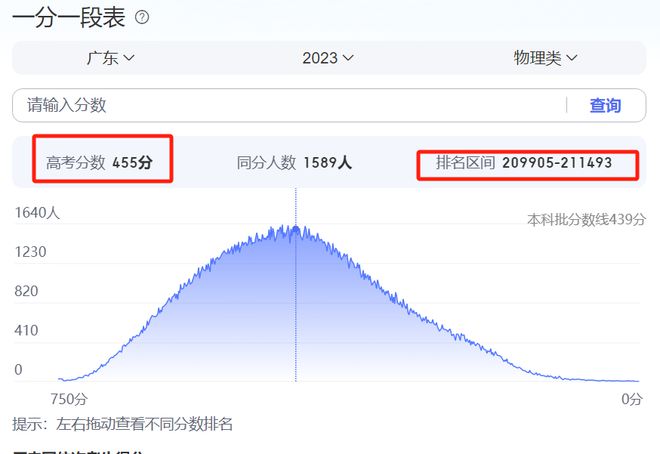2020年底,教育部颁布《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试行版《规则》”),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部专门的教育惩戒规则,也是2019年发布的《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原版《规则》”)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改后的定稿。与原版《规则》相比,试行版《规则》在制定校规校纪板块增加了有关班规制定的规定:“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家长以民主讨论形式共同制定班规或者班级公约,报学校备案后实施。”这一修改在道德教育层面具有积极意义,如果能以符合德育规律的、有创见性的形式在地方细则制定时得到落实,不但能助力教师教育惩戒权更加畅顺地行使,更能一改惩戒规则的严肃“面孔”,为其“增光添彩”。
一、共同制定班级公约的德育意义
教师组织学生和家长共同制定班级公约这一举措,既整合了班级道德氛围形成的基础要素,又融合了交往德育模式与制度德育模式这两种重要的道德教育模式,同时是消解居于一切惩戒规则核心的“过—罚”二元律令之恶的一种机制。
(一)整合班级道德氛围形成的基本要素
教师实施惩戒的目的在于对学生的不良行为予以负反馈,助力其良好纪律意识的养成。在学校和课堂中形成有利于学生自律意识形成的班级道德氛围,需要以打造学生的自主性、归属感、胜任力和公平感为基础。奖励和惩戒虽然是培养学生纪律意识的重要手段,但却不是最佳手段,容易使学生道德行为产生的动机发生偏差。培养学生基于自己的道德判断而做出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即道德自律,才是根本。这便需要学生的自主性发挥作用。归属感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也是在所属群体中获得对自我价值的认同感、建立对他人的信任感的基础。归属感的建立仰赖于个体与群体之间建立起一种相对长久的且有别于其他群体的联系。儿童的胜任力不会凭空产生,它建立在一次次难题的解决、技能的掌握以及与他人相处过程中良好关系的维持之上。胜任力不仅与学业成绩相关,而且与学校生活的方方面面皆有关联。公平感在儿童认知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通过“比较”便能自主习得。不同于自主性、归属感和胜任力,公平感是儿童普遍拥有的一种感知能力,因此也是在班级道德氛围养成中必须格外重视的一个元素。儿童早期建立了公平感之后,便会“运用对公平感的理解来评价教师和学校工作的有效性”,更重要的是“学生对教师的不公平行为相当敏感”。
教师通过组织学生和家长共同制定班级公约,能够将自主性、归属感、胜任力与公平感这四种班级道德氛围的基础元素进行整合。制定班级公约的过程,首先是学生作决策或者至少参与决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无论是教师还是家长都不能代替学生发挥其主体性,学生将就自己的价值判断作出自我承诺,为自我的行为划定边界,充分保护了学生的自主性。约束集体的共同纪律是一种特殊文化符号,这套纪律越是具有鲜明的特色,其文化符号越是强烈。教师、学生、家长三方共同制定的班级公约,既是一种同伴文化,也是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相互妥协的产物。学生参与公约制定的过程,就是将自己主动归属同伴亚文化圈并尝试理解和接纳成人世界的过程。胜任力的获得则体现在学生通过与教师和家长共同制定班级公约,产生了一种“集体解决办法”,这种办法集全体之努力与智慧,且有助于维系长久的班级人际关系,反过来又能在班级和谐相处的过程中不断增强学生的胜任力。公平感则是建立一套班级公约最原始、最朴素的职能,无论是在制定过程中共同参与,还是在公约制定后不偏不倚地遵照执行,都是对学生公平感的维护。
(二)融合交往德育模式与制度德育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育领域产生了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德育模式,交往德育模式和制度德育模式位列其中。交往德育模式主张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主体间性的交往关系”,反映“主体间的平等交互关系”,强调“学生对于社会道德规范的适应和融合应由师生共同去做,在交往对话中寻求尽可能多的共识和理解”,德育结果是“个体可以更好地认识自我和理解他人,在自我与他人之间能形成一种‘共生’关系,从而彼此获得真正的自由”。制度德育模式认为“制度德性是个体德性的基础和前提,比个体德性更具有普遍性”,要善于利用德育制度这样一种“不可忽视的德育资源”,在学校建立“符合社会发展与人的德性发展”的学校制度。
教师组织学生和家长共同制定班级公约这一举措,将交往德育模式与制度德育模式有效地结合了起来。首先,该举措打破了由校方或教师单方面制定行为规范而学生无条件遵守的传统模式,在制定公共约定这件事上给予利益相关方同等的参与权。在班级公约的制定过程中,通过三方充分的讨论,形成事实性的相互沟通与理解,并在理解的基础上达成最广泛的共识。班级公约的建立促进三方“共生”关系的形成,无论是教师、家长还是学生,都拥有了基于纪律的“真正的自由”。其次,共同制定班级公约这一规则本身便具有符合社会德性发展的积极意义,有利于在学校和班级形成共同参与民主生活的氛围。教师、家长和学生共同制定班级公约的活动便是一次民主制度的具身体验,是一次德育活动。最后,“学校和教师是受道德规则和习俗准则支配的微型社会”,共同制定的班级公约是班级这个小社会所建立的“赏罚分明、惩恶扬善的利益调节机制”,于是,共同制定班级公约的举措便是通过一种复合社会德性的制度构建起一套复合社会德性发展的制度。
(三)消解居于核心地位的“过—罚”二元律令之恶
共同制定班级公约此举对居于惩戒规则核心地位的“过—罚”二元律令之恶,既从内容上也从形式上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消解。
从内容上看,由教师、家长和学生共同制定班级公约的过程赋予了这套公约作为班级公共纪律现代契约意义上的合法性。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在其《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一书中曾明确指出:“一切惩罚都是危害,一切惩罚本身都是邪恶。”欧阳教将惩罚定义为“有意地对犯罪(过)者施以痛苦、折磨、不舒服或损失等适量的报复,以期收到社会控制的效果”。由此可见,“过—罚”二元律令天然便是有恶的,即对“过”与“罚”的界定皆仅从社会控制的视角出发,是对被控制者的霸凌。依据边沁的观点,在无据、无效、无益、无需四种情境之下实施惩罚都是消极作为,“过—罚”律令仅能维持纪律,无法实现纪律教育,而共同制定班级公约让被规范者参与到纪律制定过程中,被规范者成为规范制定者之一,基于彼此的共同诉求达成契约,对于所制定出的班级公约是一个予据、予效、予益、予需的过程。
从形式上看,无数个班级公约成为总的惩戒规则落地的具体机制,只要它们不是一个较一个更为严苛,对于总的规则反而是一种“稀释”。“当规训设施愈益增多时,它们的机制有一种‘非制度化’、从它们过去在其中进行运作的封闭堡垒脱颖而出、‘自由’流通的倾向。沉重严密的纪律被分解,变成可转换、可调节的、灵活的控制方法。”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对于以全景敞视主义形式存在的惩罚有中肯的评价,认为规训权力中的惩罚艺术不同于司法刑罚,“后者的基本功能不是考虑一系列可观察的现象,而是诉诸必须记住的法律和条文。它不是区分每个人,而是根据一些普遍范畴来确定行为”,“广泛流传的全景敞视主义使它能在法律层面之下运转一种既宏大又细密的机制,从而维持、强化和扩大权力的不对称性,破坏以法律为中心所划定的界限”。班级公约作为国家规范、校级规范下属的规范,如同毛细血管一般的存在恰恰可以在形式上保证具体规范以与中心规范不尽相同的面貌存在,而共同制定的班级公约将不同于司法刑罚,它们一定是“看见”每一个人、区分每一个人的。
二、共同制定班级公约的实践要义
要较好地落实共同制定班级公约的要求,需做到既符合德育基本规律,又有所创见,还要坚守惩戒规则制定的初衷。
(一)注重学生道德认知发展水平的差异
教育部解释试行版《规则》时指出,“高校学生已有《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予以规范,而学前幼儿认知和行为控制能力较低,特殊教育学校学生身心发展存在障碍,都不适宜实施教育惩戒”,据此规定了其适用范围。可见试行版《规则》作为一套总则,也将学生所处的不同认知发展水平考虑了进去。但是仅仅按照学段或普通校与特殊教育学校的差异来划分还远远不够。戈尔尼克等人曾经将学生的年龄划分为儿童期(早、中、晚三个阶段:早期为3~5岁,中期为6~8岁,晚期为9~11岁)、青春期、成年期,并认为不同时期的学生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努奇认为,儿童早期(学前至2年级)、儿童中期与青少年早期(3~8年级)、青少年期(高中),学生的道德发展都处于不同的阶段,对道德氛围的需求和自身的主要问题都不尽相同。皮亚杰的逻辑推理阶段认为,儿童从开始学习说话以后,要经历直观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7岁以后)以及形式运算阶段(青春期后),不同阶段逻辑推理能力都不相同。科尔伯格将道德认知水平划分为前习俗水平、习俗水平和后习俗水平三种以及各自包含的两种阶段,合起来是他律道德、个人主义、人际关系、社会系统、社会契约、普遍性伦理学原则等六个阶段。它们不完全与不同年龄阶段对等,同一年龄段人群的道德认知发展可能处于不同水平。无论是哪种理论,都说明中小学生这一群体中的个体,其道德认知发展水平并不相同,用同一套纪律体系进行规范或许力有不逮。
制定不尽相同的班级公约本身就是对不同道德认知发展水平的学生进行纪律意识培养的良方。在公约制定过程中,教师和家长既要充分考虑学生所处的年龄段特有的语言表达水平、逻辑思维能力水平,引导学生表达自己的纪律诉求;也要考虑班级里每一位学生的道德认知发展水平所处的阶段。班级公约的道德水平超出多数学生的道德认知发展水平两个阶段以上,或是平行、低于多数学生的道德认知发展水平,都不利于现有水平的提升。针对不同道德认知发展水平制定专属的班级公约,还能保证惩戒措施有的放矢。
(二)将奖励一并纳入公约制定的考量范畴
教师、学生和家长三方共同制定班级公约时,要避免使其沦为具体的惩戒条例,而应是一种彰显班级文化的“公共约定”,是该班级的专属纪律。对不良行为进行惩罚、对积极行为加以鼓励,是促进纪律氛围逐渐形成缺一不可的教育手段。试行版《规则》是针对不良行为的规范,对于如何鼓励积极行为并未加以规定。但遵从试行版《规则》背后的制定逻辑——对不良行为不可不作回应,也不可滥作回应,对于鼓励积极行为同样既不可视而不见,也不可令其沦为“控制表扬”,改变学生产生积极行为的动机。奖励的数量和形式如何能够更大限度地符合班级纪律文化氛围的生成,非师生及家长共同探讨而不可得。
“奖励与惩罚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19],仅就惩罚实践讨论惩罚问题,往往容易忽视奖励实践导致的惩罚效果。在某些情境下,奖励与惩罚甚至还会同时发生,或者造成与表面行为完全相反的作用力,这种情境常见于言语性奖励。某些情况下,因奖励而导致的“惩罚效果”会作用在被奖励者关系人群身上。例如:两名学生同做某一合作研究成果展示,教师表扬了其中一人,没有受到教师表扬的另外一人则可能会将教师对同伴的表扬诠释为“老师认为我的表现乏善可陈,所以没有表扬我”的意思,其内心的状态将无异于受到了教师的批评,尽管教师并没有对其做出批评的事实动作。还有一种情况,因奖励而导致的“惩罚效果”作用在被奖励者本身。例如:一场考试过后,鉴于同桌两人一贯的成绩表现,教师对其中一位学生说:“这次考得很不错,进步不小!”转头又对另一人说:“你这次没发挥好,这不是你的水平。”如果两人的考试成绩相差无几,这时被表扬的同学极有可能将教师对两人的不同评价解读为“老师是想说,他本应比我强很多”。这样的案例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不胜枚举,听话者“并非有意识地顺应某种教育境况的方式规定解释性的理解过程”,对话并没有形成。共同制定班级公约时将奖励与惩戒一并拿出共同讨论,通过讨论(对话)达成深层次的相互理解,即达到师生的视域融合。教师和家长重新认识学生的真实诉求,学生更加理解教师的言行或有局限但实无恶意,有利于避免教师的惩戒行为因为对于被惩罚对象及其利益相关者的感受有欠考虑而导致结果背离其初衷。
(三)坚守惩戒初衷
教师组织学生和家长共同制定班级公约有多种形式,可以在师生熟悉彼此脾气秉性之后再着手“量身定制”,也可以用一个漫长的过程对公约进行逐步完善,但教师须在此过程中坚守惩戒规则颁布的初衷:“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保障和规范学校、教师依法履行教育教学和管理职责,保护学生合法权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试行版《规则》第一条)。也就是惩罚不是目的,而是保障前述一切目的的手段。
我国古代奉行“不打不成才”,严苛的训诫方式在传统教育中鲜遭质疑。随着《儿童权利公约》的颁布,我国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师德建设的法令,严禁教师体罚学生。1993年10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体罚学生且经教育不改的”属于违反师德红线,由所在学校、其他教育机构或者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2012年2月教育部发布的幼儿园、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也将“不讽刺、不挖苦、不歧视”“不体罚或变相体罚”等列为师德底线。加之学生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日益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一线教师无论是基于教育理念还是基于对惩罚学生所要承担后果的畏惧,都不敢行使惩戒权。在这样的背景下,或因畏惧或因“取悦”学生和家长,共同制定班级公约时教师有可能一味退让,这样的班级公约将失去惩戒的德育价值,也无法真正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缺失主体意识的人不可能走向全面发展,而现代意义的人本主义已经不同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概念,“真正意义上的人”要能“领悟人自己生存发展的意义和价值,超越物之上,以寻求解决社会危机和人的精神危机的路径”。因此,现代意义上人的主体性的获得更加强调自律精神的获得,以培养自律精神为目的的惩戒公约恰恰是对现代意义上人的主体性的保障。
教师的权威与个人魅力对于惩戒实施的方式和效果有极大影响。“真正厉害的教师,既不是唠唠叨叨的教师,也不是廉价奉承学生的教师,更不是时下冒尖的媚学生俗的‘名师’,而是举止庄重的教师。这样的教师,不表扬、不批评则已,一旦开口,容不得学生不予重视。”因此,教师可尝试在师生有了进一步了解之后再行制定班级公约,有针对性的讨论更有利于界定体罚的边界在哪里、真正能令这个班的学生产生羞耻感的惩戒行为是什么等对于公约制定至关重要。而公约一旦制定,便应遵照执行,以保证其权威。“当学生从教师的行动中意识到某种规范只不过是挂在墙上的条文或‘说说而已’,仿佛是举在手上的棋子,那么,这种规范就无权威可信;反之,当他们感受到某种规范不可侵犯时,这种规范才具有权威的力量。”
来源 | 《中国德育》 2023年第19期
作者 | 盛夏(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